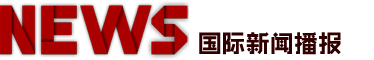泸溪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学生正在跳竹竿舞。袁庆国 摄

泸溪县乡村景象。 袁庆国 摄
泸溪县位于湖南省西部,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南端,沅水中游,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、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五强溪水电站移民库区县、国家级贫困县和革命老区县。全县11个乡镇147个村(社区),总面积1565平方公里,总人口约32万人,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达62%。
泸溪,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山深处,是一个少数民族占62.3%的民族县,一个至今不通火车的移民库区县,一个2018年财政经常性收入不到5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。就是这样一个县,却办出了老百姓认可、师生都不愿意走的教育。
——全县每年约3.8万名中小学生,择校到外地上学的人数几乎为0,相反,目前在县内就读的外县籍学生有2075人。
——近年来,几乎没有一名教师被“挖墙脚”。2019年,全县调出教师4人,调入则达24人。而且自2010年以来,全县先后有300多名教师自愿申请到乡村学校任教。
——几乎没有一人辍学,2019年,全县学生巩固率小学100%,初中99.5%,高中99.62%,初中学业水平检测名列全州前茅。2016年以来,全县共有2928名学子考入本科院校,其中14名学子考取清华北大,本科上线率、本科上线万人比,连续14年位居湘西州第一。
2018年,泸溪以优秀等级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,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批示:“泸溪经验很好,要推广。”
泸溪经验是什么?为什么会逆势飞扬?凭什么?怎么做到的?原因何在?中国教育报记者十几次深入泸溪,见证变化,寻求答案。
教师为什么“挖不走”?因为“世界我最牛”
在泸溪工作了28年的泸溪二中校长杨顺旗说,县里从2016年开始,教师节表彰有一个隆重的“走红地毯”的仪式:县城主干道交通管制,警车维持秩序,鼓号队演奏,所有被表彰者披红挂彩,接受众人的欢呼和注目。这种“红地毯”,杨顺旗走了两次。“不在钱在荣誉。”他说,那一刻,“世界我最牛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都说乡村教育最难的是教师队伍建设,教育局局长最痛苦的是优秀教师“进不来、留不住、干不好”,泸溪就没有过这样的烦恼?
当然有,但泸溪人以自己特有的努力,一一化解。
1.提待遇建住房,为乡村教师创造“牛气”的工作条件
“世界我最牛”是心理感觉,其实泸溪教师队伍的基础并不牛。
先看一组数据:
全县2937名在职教师,从学历上看,研究生24人,本科1687人,专科1067人;
从职称上看,正高3人,特级3人,副高531人,中小学一级二级2298人,占绝大多数;
从类别上看,毕业于师范专业的教师比例也不高,只占67%,其他均为非师范类专业毕业,其中特岗教师183人。
这是一支整体学历并不高的队伍,毕业于重点高校的少之又少,90%的教师毕业于地州市一级的本专科院校,湖南师大能来一个毕业生,那都是县里的“掌中宝”。
与全国其他偏远贫困县一样,泸溪很难招来优秀毕业生当老师。2016年该县制定人才引进政策,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和“985”“211”学校的毕业生都给予一定额度的安家费,但3年多了,也才引进来28人。“毕竟交通太不方便,经济也不发达。”县教体局局长谭子好坦陈。
但只要人到了泸溪,就几乎很少有离开的。
为什么?房子、票子、位子?是这陈俗的老三样?是,又不是。
先说“是”的部分。
对泸溪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早在2009年,泸溪就在全国率先实施乡村教师津补贴,当时村小教师每月能额外多拿300元。从2012年开始,这个数字大幅提高,村小教师每人每月最多能多拿1400元,乡镇完小、初中教师能多拿500元,县财政每年安排补贴资金达1846万元。
“盘子不大,当然好办。”可能有人会这么说。泸溪盘子是不大,总人口才31.7万,但要知道,2012年泸溪全县的财政收入才3.1亿元,农民人均纯收入才4089元。
“也是被逼出来的。”2013年11月,县长向恒林在被点名参加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时说。
泸溪有175所学校,乡村学校就有167所,其中还有教学点88个;泸溪县在编教职工2937人中,就有乡村教师1989人。和全国许多农村县一样,2009年前,泸溪县教育局每年收到的进城报告有400多份,占乡村教师五分之一。教师大量往城里涌,乡村学校渐渐成为“空壳”学校。
泸溪人下决心改变。2009年,在时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杜晓勇的主持下,县政府出台了正式文件,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。
仿佛有了一支无形的指挥棒,这之后,不仅教师们愿意留在乡村,甚至还出现了教师配置“城乡倒流”的现象。2010年以来,共有300多名教师申请到乡村学校任教。
2014年,马王溪小学出现空缺岗位,中心校有6名教师竞争报名,今年40岁的周元英以过硬的教学质量,竞聘到了这个岗位。“不包括五险一金,一年能到手7万多元。”周元英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。她说,她与丈夫刘克齐都在马王溪小学,两人加起来年收入有15万元。
如果说教师津补贴让泸溪乡村教育振兴迈出了第一步,那么,教师公转房的建设就是第二大步。
在湖南乡村任过教的都知道,乡村校是没有每天下班回家一说的,基本是周日下午到校,周五下午才能离开,其间基本都要住在学校。几千名教师,学校哪有这么多房子?于是住教室的、住实验室的、住闲置房的,甚至住危房的,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。2006年,湘西启动教师公转房建设,学校出地皮,教师出部分资金,泸溪3年里建起了426套教师公转房,但还是有好多教师没房住。
可要全部解决,一两千套,即便按最低价最小面积,投入也是数以亿计。钱从哪里来?泸溪创造性地整合各方资金,甚至将廉租房建到了学校,终于,从2011年开始,1643套廉租房、216套公转房,哗啦啦在几十所学校出现了,全县乡村无房教师人手一套。记者在兴隆场镇中心小学看到,24岁的青年教师舒洪波,住在两室一厅一厨一卫50平方米的廉租房里,尽管不是很大,但收拾得利利索索,“城里这一套得几十万,4年前我刚毕业就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,虽然有点偏、离家远,但我真的很踏实。”舒洪波说。
2.留人更留心,为乡村教师营造“挺直腰杆”的“牛气”氛围
再说“不是”的部分。
在泸溪,教师是轻易“挖不走”的。这里有一组直观且能说明事实的数据:在全县2937名教师中,有300多人来自外县市,但近5年来没有一人回去。2019年,调出4人,调入则达24人。
莫顺清,湘西州首府吉首某校来挖他,年薪20多万,还给一套房子,不去;
田云坤,凤凰人,还是吉首某校要调他,开价是年薪十六七万,不去;
李建军,两口子都是外地人,有学校出高薪要两人一起调,还是不去……
教师有尊严、有地位,这在泸溪已经真切地形成了一种文化。“老师们在意的其实不是钱,是这份尊重,让他们挺直了腰杆。”谭子好说。
怎么尊重?这个尊重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,一是官方的,干得好就有奖励有前途有位子;二是民间的,孩子出息了教好了老百姓口口相传,老师们走到哪都能自带“牛气”。
在泸溪,“有为就有位”,不是一句空话。
尽管是当年少见的湖南师大毕业的本科生,28岁时就在泸溪五中当教导主任,但因为身体不太好,县一中德育主任杨顺旗一直没想着要有多大发展。突然有一天,谭子好找到杨顺旗,希望他出任二中的校长。他很是意外,当即婉拒。
一年后,谭子好再次找到他,再次说明理由:为什么看中你?因为几次晚上去一中,看到你晚上九十点还在阅卷,勤奋;当时和你说话,发现你当了6年中层,仍无倦怠之意……
杨顺旗没想到,自己的付出,领导都看在眼里。2017年他到二中后,像打了鸡血一样,又当校长又带班还给学生义务补课。“我热爱这份事业,无论平凡、无论贫穷。”他的办公室墙上,挂着这样一幅自己写的字。
2006年从吉首大学毕业的李建军,主动申请当班主任,带的班非常出色,2014年还创造了一中新纪录——班上培养出了3名清华北大学生和一名空军飞行员。他做梦也没想到,2017年,不到35岁的他,会直接从教科室副主任提拔为县五中校长。
对教师体贴细致的关爱,也是尊重的一个重要内容。“几乎走遍了每个村小。”这是县教体局一位干部对书记、县长和分管教育副县长的悄悄观察。
“有家的感觉。”来自辽宁鞍山、已在泸溪二中工作了7年的物理教师杨德尚,谈起自己这7年的点点滴滴,谈起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,30岁的大小伙子眼泪都流了下来,但是擦干眼泪他又补充:“因为在泸溪,领导人人有服务意识,老师有什么困难,都不用自己张嘴。”就在记者采访时,谭子好还准备给他介绍对象。
来自乡亲们的尊重和厚爱,故事更是多得写不完,记者在白羊溪乡土家山寨报木坨村,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:
2012年4月,正在上课的报木坨村教学点教师杨润生倒在讲台上,州医院诊断是患胸腺瘤和重症肌无力,需马上送省级医院手术治疗,估计需10万元治疗费。
报木坨村的乡亲们主动地你借1万元、他拿5000元,村里最年长的李阿婆把自己卖野葱和南瓜花赚来的200多元钱也掏了出来。众乡亲相凑,加上学区捐款,杨润生的手术费第二天就凑齐了。
杨润生有一个账本,上面写着:欠覃天林10000元(已还2000元),欠覃民秋8000元(已还500元)……“账本上的钱,我这辈子还不尽,只有把乡亲们的孩子都教好了,都教成才了,我心里才舒坦!”杨润生两眼红了……
3.提高专业素质,让教师有底气“牛气”
有好的教师,才有好的教育。
“教不好”,教师“牛气”哪里来?何谈振兴乡村教育?
抓教师成长,第一就是树立质量导向。
对于泸溪教育来说,教育系统有3份最重要的文件,分别是《学校目标管理考核方案》《教学质量效益评价方案》《校长目标管理考核方案》,发奖金、给表彰,全看这3个方案落实得如何。其中,教育教学质量都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,占据着重要考核比重。
之前说到的村小津贴,并不是只要在村小教书就每月能多拿1400元,而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。县里每学期有个大型的质量检测,检测结果靠后,对不起,不要说评优晋级,连报名参加调动考试的资格都没有。
也正是在这样的指挥棒下,泸溪的教师们人人想办法提高教学水平,人人想办法练“手艺”。
第二个做法是典型引路,加强师德师风教育,最大程度唤醒和激发广大教师的责任感。
泸溪教育质量不错,有补课吗?当然。但那都是按规办事,所有教师,绝对不允许“家教家养”,绝对不允许到各种培训班兼课。近3年全县也辞退了5名违规教师。
泸溪教师们的敬业和奉献精神让人感动,谈起自己的工作,谈到自己的学校,谈起自己的学生,几乎个个热血沸腾,激情满怀。
80后符海鸥,把孩子留在县城让家人带,自己来到远离县城50多公里的黄泥冲小学,现在已经坚守了7年。她曾经接手的一个班,三年级42名学生,语数平均分只有30多分,有好几人只有几分。符海鸥找来低年级教材,从加减法开始讲起,天天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辅导。2016年,这个班级语文平均分达到了80多分,数学90多分,排名全县第二。
一中数学教师兼班主任张昌能,一心扑在班里40多个孩子身上,他为班上所有的孩子建立了详细的档案:兴趣爱好、学业成绩、人生目标,但自己读初中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却长期放在岳母家。
谭子好把符海鸥、张昌能这样的教师,叫作“泸溪教育筑梦人”。他认为,只有这样的“筑梦人”越来越多,泸溪振兴乡村教育的梦想才有可能成真。
泸溪的第三个做法,是加大培训力度,推进挂职轮训,“名师带徒”,结对帮扶。
泸溪有各类中小学175所,但大的学校也就31所。这些年来,这些“大校”的校长们几乎全都送到外地跟班学习过,县里每学期会选送2—6名校长、10—20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发达地区名校挂职锻炼、跟班学习。五中校长李建军,就被送到州里的“班主任骨干班”进修,到湖南最著名的师大附中跟班学习。“进步不是一点点,是一年一个台阶。”李建军说。
武溪二小副校长张世全,从北京朝阳区朝师附小跟班一个学期后,回来就在学校推行“三三微行为”,张世全说,全校338名学生,90%是留守儿童,30%多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孩子,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是他们的工作重点。“都是从北京学来的。”张世全说。
财力有限,更多的“送出去”不可能,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培养培训,来自县教体局的数字是,从2015到2018年,3年来全县完成教师培训1.2万人次。

(责编:郜林筱、陈康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