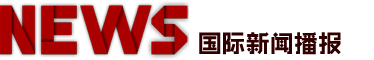来源:巴中新闻网 编辑:刘波 更新时间:2015-10-13 ——巴州区大河乡界牌村人文历史述略 (文.图/张浩良) (一)



爆料电话:0827-5222111
邮箱:bzwlcm@163.com


您当前的位置:地方频道-巴中 > 巴中要闻
秦巴古道第一村-巴州区大河乡界牌村人文历史述略

云雾曼眇
界牌村行政隶属四川省巴州区大和乡,地处巴州区东北一隅, 北纬N30°45′,东经E125°40′。属大巴山南麓米仓山东段缺口延展逶迤而至的丘陵地貌特征。东北部与通江杨柏沙泥坪村、火炬连接,西北部与官渡、火炬接壤,东南部与花溪乡天井村交界,西南部与大河乡 村毗邻。如今全村幅员面积8.2平方公里,人口1065人。
界牌村岭壑交错,冈峦丛杂,居山之巅,为巴州出境东大门。特殊的自然地理,自古以来,秦巴古道穿行山脊三十余里。境内海拔600——800米,属亚热带季风气候,春暖夏凉、秋风冬寒的气候特征。日照长,早春和秋季风大,冬季寒冷,四季分明;年均气温18.5℃,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831小时,无霜期223天,年总降水量1522.8mm。立体气候明显,适合多种物种生殖与繁育。沙回坪(杀牛坪)、红碑梁、何家梁等山脊提纲挈领,构成山岭相携田畴相间的山地台塬,主要成土母岩为砂岩,土壤多为黄壤、沙壤土。全村有土地面积1200余亩,粮食作物以水稻、小麦、薯类为主,养殖业以猪、牛、鸡、鸭等动物为主。
境内林地面积大,物种丰富,森林植被以柏树、麻栎、马尾松、化香、夜合、檀木、黄荆、蔷薇、马桑、荚蒾、柴胡、前胡、苔草、狗尾草等构成的主要建群种,森林面积近万亩。森林覆盖率45%左右。人工栽植的古柏群保留285株,此外村民房前屋后及道路植树风气由来已久。鸟类、狗獾、野兔、蛇类、昆虫(蝶、蜜蜂、蜡虫)、鱼类等动物资源丰富,初步统计分析全村有动植物资源(药材)千余种。栽植植物五十余种,养殖动物10余种。
此外,山川灵异,自然景观独特。石锣、石鼓、石笋、石鸟(斑鸠)、石窟、石窦,龙盘虎踞,构成境内大小数十处自然文化遗产;自然风光旖旎,水域沟壑相间,风生水起;山岭星罗棋布,九龙捧圣,犹如青螺翠髻,宛如世外桃源。
界牌村历史以来,隶属于巴州(县、区)辖区。巴中县古隶禹贡梁州之域。春秋时为巴子国,秦灭巴蜀,于其地置巴郡。汉因之,列郡境为宕渠等十余县。后汉和帝永元中,分宕渠北界置汉昌县(今巴州),仍属巴郡。三国、晋属巴西郡。后周大象二年,改梁广县曰化成,仍为巴州大谷郡治。隋初大谷郡废,大业三年改巴州为清化郡。唐高祖武德元年复曰巴州,玄宗天宝初又为清化郡,肃宗乾元初复为巴州,属山南西道。五代蜀因之。宋曰巴州清化郡,属利州东路。元曰巴州,属广元路。明洪武九年省化成县入州,寻又改巴州为巴县。武宗正德十年复曰巴州,属保宁府,清因之。民国二年改为巴中县(《巴中县志》1927年)。
明清之际,界牌村成为巴州(巴中、通江县)分界线,立有官府区域分界碑(村民沿界牌交错分布),界牌村因此始名。清宣统以前巴州设十一乡,界牌村隶属于明山乡四甲地。民国隶属于清江渡乡(领中兴、大罗塘、丝连垭、新庙子、板凳垭、新场),为大罗塘管辖。1949年政权变更,界牌村隶属大和乡至今(政权变更必然导致通、巴两县村民属地的微小变更),随着土地权属和方便,辖区村民及土地隶属略有调整。
考察当地区域地名,见诸文献者可上溯三国时期,此地始称沙回坪(后蜀程姓始祖程琼隐居地),此后世称沙回坪或沙泥坪,因其境内成土母岩为砂岩,沙壤土形成及流失过程而得名(见于程氏宗谱、清代墓碑),后来嬗变谓沙牛坪或杀牛坪。亦说明清时代古道商旅往来频繁,战乱不断,古道牲畜贸易、店铺及市场沿古道增多;正义之师与匪患交织,起义与流民难辨,界牌村成为战乱重灾区,战争的血腥牲畜也未能幸免,杀(沙)牛坪因此而名(“牛坪”一名,见于清代墓碑)如今,杀牛坪属于大和乡三村亦称“界牌村”。沙回坪山脉属于大巴山脉逶迤至通江西部山脉延伸,据民国续修《通江县志稿.山脉志》云:“石门寺山脉自石垭子分支南延为马家寨(一名天成寨),经双凤垭(山下有清进士朱昱父子墓)、沙泥坪(在治西七十里)南入巴中境为明山(在巴中花溪河西),别支南行讫于大罗塘。界牌村位居“双凤朝阳”(在治西八十里双凤垭,前后两山各舒凤翼,中有圆峰如日轮,俗呼双凤朝阳)和通江西至巴中县要道(由治城三十里鹦哥嘴,三十里杨柏河,十五里沙牛坪接巴中县界,一百零五里巴中县),为通江入巴中之要道,为旅省及赴嘉陵道署必由之路。”所以南来北往的政要、商贾、将士、行旅频繁驻足的要冲,讫于1958年。
界牌村二、四组沙泥坪山顶周围(面积180000平方米)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。该遗址属于山地文化类型,与龙山文化同属一个类型。据此可见,界牌村距今有5000年人类悠久历史。
秦汉以来,这里是秦巴要冲,是米仓古道的起始点(神经末梢),是秦蜀商道和古驿道,境内留下大量先民文化遗存,如古驿道(古道石级)、岩墓群、墓葬群(石棺及土葬)、古佛龛、客栈遗址等,至明清、民国时代,丰富的社会、经济、人文历史,史不绝书,伴随人类社会进化(治乱)的脚步,走向现代文明。昔高祖为汉王时,发巴郡夷人伐三秦既定,乃遣还复其渠,帅罗朴督鄂度席龚七姓,不输租赋,余户岁入賨钱,号为板櫈夷。按板凳夷谓赋为賨,故呼为賨人。后汉张鲁据汉中,与刘璋为敌,璋以庞义为巴郡太守屯阆中以御鲁。义辄召汉昌賨民为兵(《巴中县志·拾遗》p22)。自汉晋以来,没于群獠抢攘,于齐梁魏周,故唐世统一,特简重臣镇其地,天宝末年夷獠乱之,宋乾德重文协侵之,元至正中明玉珍陷之,兵役不已,继以盗匪,要以明末为甚。明武宗正德四年,保宁贼蓝廷瑞自称顺天王,鄢本恕自称刮地王,其党廖惠称扫地王,众十余万,置四十八总管,延蔓秦楚间,转寇巴州,人民死亡过半。明崇祯十年,张献忠乱蜀至顺治三年,献贼伏诛,“其间州中无主凡七年”。明末的“姚黄之乱”,乾隆六十年及嘉庆元年至七年白莲教起义,咸丰十一年“朱逆之乱”多次犯境,1933至1935年,这里大小战役5次,界牌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界牌村特殊的战略位置,凡欲酝酿历史开头,或觊觎天下者,战乱硝烟进退必扰,也因此饱受战火的洗礼。境内至今留下了可资凭吊的文化遗产,成为界牌村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或徽记。